

对证据的审查以及对证明规则的运用,古已有之。无论是“众证明白,即同狱成,不须对问”,还是“若赃状露验,据状断之”,抑或是“ 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历代法典中鞫狱断刑、解决纠纷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任意施为之事,而是必须做到有理有据,令人信服,这就要求司法官员必须有一定的证据意识、遵循一定的证明规则。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大量案例判词凸显出南宋时期名公审理案件时的裁判理念、裁判方法,特别是对证据的重视以及对证明规则的运用。以下先试举一例:
名公翁甫(号浩堂)审理了一起《买主伪契包并》案。寡妇阿宋有三个儿子,长子黄宗显,次子黄宗球,小儿子黄宗辉。户下的产业除三分均分外,留下门前池、东丘谷园和池一口,作阿宋养老之用。嘉定十六年,黄宗球将东丘谷田三分中的一分,出典给黄宗智,有干照(契约文书),并且有母亲及牙人作证,其余的两分,即黄宗显、黄宗辉之产不曾出卖。阿宋诉于官府,称黄宗智欲强占其业。而黄宗智拿出一份嘉熙元年、有其余两兄弟黄宗显、黄宗辉签名的典契,称三分田产均已典卖给他。
两份典契(文书),两种不同的说辞,判官该如何判决,依据什么来辨别真伪并作出裁判呢?原判词如下:
据阿宋初词,以为黄隅官宗智强占其业。黄宗智供状,则以为并已买到。及索出嘉熙元年契一纸,但有黄宗辉、黄宗显押字,即无牙人,不曾有母亲阿宋知押。以黄宗显字画考之供状,已绝不同。又据阿宋称,黄宗辉系乙未年身死,今上件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兄弟押字不同,又不取母亲知押及牙人证见,弊病百出,不容遮掩。此皆是黄宗智用心不仁,欺阿宋一房孤寡,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使阿宋不能扶病力陈,官司不与尽情根理,则此田遂陷入黄宗智之手,使孤儿寡妇坐受抑屈,岂不可怜。黄宗智立伪契占田,勘杖一百,真契给还,伪契毁抹附案。仍给据与阿宋照应。
判官之所以认定黄宗智伪造田契以占他人之田,主要就是基于对“证据”,即两份典契的审查。在仔细核验、辨明真伪的基础上,判官查明实情为黄宗智“因得黄宗球一分之业,遂假立弊契,欲包占三分”。从案件的分析论述中,可以看出:
首先,在证据类型上,南宋时期的证据不仅已有书证、物证,还有证人证言,勘验检查笔录、鉴定结论等。本案涉及的书证和证人证言中,二者的证明力也有高下之分。按照《宋刑统》规定,“典卖指当论竞物业”,“应有将物业重叠倚当者,本人、牙人、邻人并契上署名,各计所欺入己钱数,并准盗论。”宋代土地田产买卖典当需要订立契约,需要有本人、牙人、邻人在契上署名。经过官府投税印押的契约,称为“红契”或“赤契”,而私下订立没有经官投契的,为“白契”,不受法律保护。名公吴恕斋曾说,“官司理断交易,且当以赤契为主”,“必自有官印干照可凭”,而“白契不可凭”。从这一点来看,现代证据规则对此仍有沿袭,比如经过公证的书证、公文书证证明力更高。
其次,证据审核认定上,在审查证据三性的真实性上,本案也值得称道。从形式上看,黄宗球与黄宗智签订的典契形式完备,不仅有签字,还有母亲阿宋与牙人作证。而黄宗智拿出来的嘉熙元年的契约,既没有牙人的署名,也没有阿宋的知押,与当事人之一的黄宗显的字迹也不一致;从内容上看,黄宗智的契约上只有两兄弟黄宗显、黄宗辉的签名,没有母亲阿宋和牙人的署名,依常理推断,不符合当时田产典卖的一般规矩。更重要的是,另一当事人黄宗辉在乙未年已经死去,而“契书乃在黄宗辉已死之后”。种种迹象表明,第二份契约的内容不合乎情理。
再次,从证明过程看,判官在判断证据及其证明力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以证据为基础勘测案情,力求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所谓“事有似是而实非,词有似弱而实强,察词于事,始见情伪,善听讼者不可有所偏也。”各种证据综合审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相互印证,才能查明案件事实。本案中翁浩堂也同样并未依据书证这种单一证据,而是结合了证人证言,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经验等综合进行判断,最终形成内心确信,正是善听讼者之所为。
最后,在作伪证惩戒上,本案认定“黄宗智立伪契占田”,翁浩堂不仅支持了原告的诉求,同时还将伪契毁抹附案,并对伪造证据者“勘杖一百”,这对抑制伪造证据、作伪证等行为起到了很好的惩戒效应。类似做法在《清明集》的《物业垂尽卖人故作交加》《兄弟争业》等多个案件中均有体现,反映了判官对伪造、毁灭证据,提供虚假证据等行为进行惩戒的倾向。
“据证定罪”,不偏听偏信,注重审查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朱熹有言,“或旁无佐证,各执两说。系人性命处,须吃紧思量,犹恐有误也。”与前朝相比,宋代对证据的重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司法实践中对证据的辨别和运用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升;《洗冤录集》这部法医学著作的问世与应用,更是帮助司法官员在案件事实认定上实现了质的飞越。但仔细思考,尽管已经取得如此成就,是否可以说南宋时期已经形成较为科学的证据制度?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以下再举《邻妇因争妄讼》一案的判词为例:
观阿周状貌之间,必非廉洁之妇。与尹必用比屋而居,寻常升堂入室,往来无间,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则未有不从者。今阿周乃谓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闺之中,抗拒得免,逃遁而归。此必无之事也。若果有之,何不即时叫知邻舍,陈诉官府,必待逾年而后有词,则其为妄诞,不言可知矣。大凡街市妇女,多是不务本业,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三五为群,专事唇舌。邻舍不睦,往往皆因于此。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真此曹之谓也。阿周今至讼庭之下,太守之前,犹且谗谤不已,略无忌惮,况在家乎?决竹篦十五,押下本廂,扫街半月。尹必用今后亦当安分守己,亲善邻舍,不许因此得胜,妄生事端,如再惹词,定当惩治。
此案的原告阿周是一名妇女,状告邻居尹必用,称自己被他抱持于房闺之中,幸而全力抗拒,最终方得逃脱。与前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判官胡石壁认定阿周妄诉,所依据的仅仅是三个推论。一是“观阿周状貌”,看出她“必非廉洁之妇”。为支持这一论述,胡石壁指出,阿周与尹必用比邻而居,却并不懂得避嫌和自重,“升堂入室、往来无间”,认为阿周其人“特患尹必用不能挑之,则未有不从”——这是根勘已知行为,推定未知行为的逻辑。二是如果阿周真的被尹必用抱持于房闺之中,就应当即时叫知邻舍,到官府起诉,为什么逾年而后有词?——这是根勘行为动机,推定案件事实的逻辑。三是阿周到了判官跟前,仍然喋喋不休、谗谤不已,何况平时在家呢?这一定是一个口舌之妇——这是根据阿周的庭前表现,把已发生情节当做佐证,进一步巩固已有结论的逻辑。三层推论尽管看上去有理有据,然而细察之下,却并无明确的证据支持。尤其判官从原告样貌、平时举止就推断其“必非廉洁之妇”,更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以看出,尽管是原情定罪的需求,然而本案对品格证据的运用几乎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在科学性、公正性上的瑕疵也不言自明。
上述两个案件对比可以看出,南宋时期,一方面判官审案认定事实仍然坚持以证据为基础这一基本原则。“大凡官厅财物勾加之讼,考察虚实,则凭文书;剖判曲直,则依条法,舍此而臆决焉,则难乎片言折狱矣。”证据是考察虚实的基础,条法是剖判曲直的依据,二者缺一不可,否则通过主观臆断,难免作出不公正的裁决。然而另一方面,在没有证据的特殊情况下,比如,案发时只有当事人双方在场、缺乏其他旁证的案件,如辱骂长辈、强奸未遂、猥亵妇女等,一般是根据推理、义理等作出审判。可见在司法的特定场域,判断案件事实主要还是依靠法官的个人决断。
西人韦伯将中国传统司法审判归结为“卡迪审判”,即裁判者通常诉诸法律之外的灵魅、情感、伦理关怀、政策考量以及抽象的社会正义观。尽管古代判官的裁判“带有具体权衡的特色”和个案裁量的特性,但据证定罪仍是一条基本规则。即使在没有证据予以佐证的案件中,法官也并非是任意自由裁量的,而是必须受到当时社会公认的情、理、法的多重制约,受到“礼”的约束,服从于普通民众对案件客观真实的追求和对实体正义的渴求。总的来说,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南宋判官通过审查证据对事实进行评价,进而与法律规范相联系,最终使案件的裁判达到了酌人情而循法意的效果。
作者:王爽(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来源:人民法院报
【往期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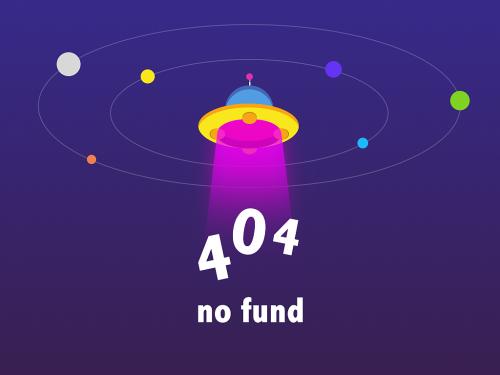
凡本平台发布的内容,尊龙app的版权均属于滦南融媒,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利用。已经本台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滦南融媒。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台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侯新宏主持召开我县草制品加工专项治理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和县土地管理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
侯新宏主持召开我县草制品加工专项治理行动动员部署会议和县土地管理委员会2022年第一次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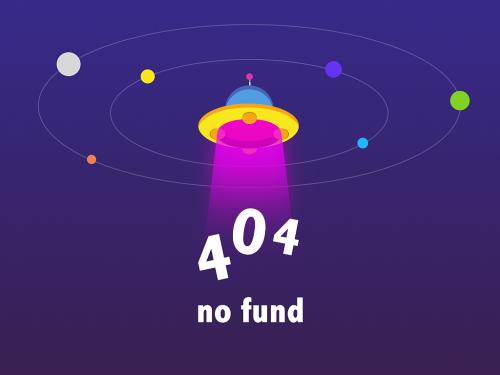 我县召开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命令会议
我县召开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任职命令会议
 【特别关注】消费者权利有哪些?怎样维权?
【特别关注】消费者权利有哪些?怎样维权?
 【特别关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内循环“消堵”
【特别关注】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为内循环“消堵”